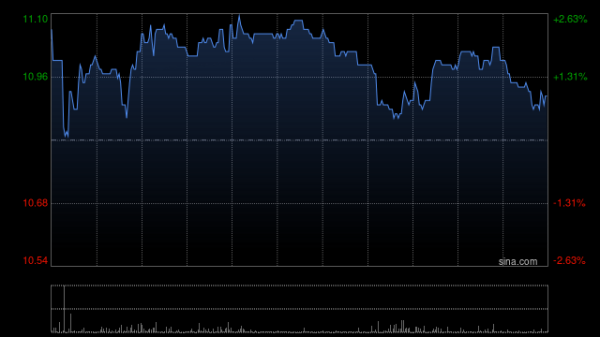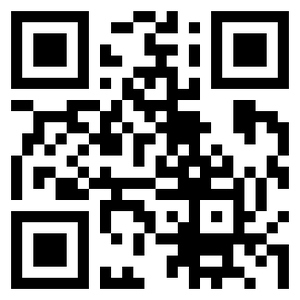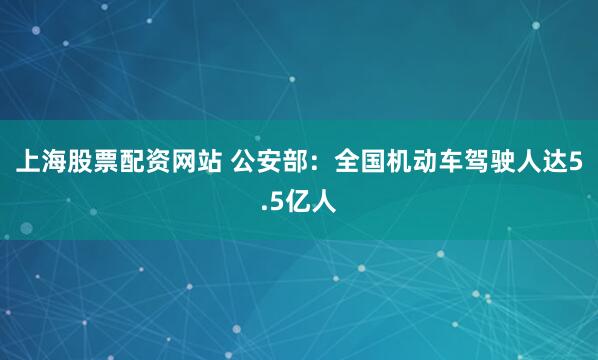1942年,在东极岛的波涛汹涌中,198名中国渔民驾驶着简陋的舢板,毅然冲破日军的严密封锁,成功营救了384名英军战俘。这一壮举,曾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八十余载,几乎被遗忘。然而,历史的真相永远不会沉没。电影《东极岛》以“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为蓝本,以艺术手法再现了当时中国渔民的义举,让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再次闪耀在世人眼前。
人性之光永不磨灭
文|王卓奇
电影《东极岛》以其沉稳扎实的叙事手法和恢弘壮阔的视听语言,将一段被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真实故事搬到了大银幕上,这部电影不仅是对战争年代的郑重回望,更是对凡人善举的深情礼赞。
电影《东极岛》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自始至终关注的都是宏大叙事背景下的个体叙事形态,又以小人物的个人成长,来反映大时代的理想信念和抗争精神。演员朱一龙饰演的渔民阿赑隐忍克制,在目睹日军的残酷暴行后,其内心深处的正义感被逐渐唤醒,最终蜕变为一个视死如归的抗日英雄;演员吴磊饰演的渔民阿荡热血赤诚,他坚信所有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英军战俘跳船逃生,自己则在枪林弹雨中壮烈牺牲;演员倪妮饰演的渔民阿花坚韧倔强,为了拯救落水受困的英军战俘,她毅然打破了“女人不能出海”的行规戒律,率领东极岛全体渔民开船驰援。
展开剩余71%出于尊重史实的需要和艺术创作的诉求,电影《东极岛》剧组提前在舟山群岛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总共收集了数十位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亲历者后代的口述资料,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发当年的历史场景和人文风貌。从天高地阔的浙东渔村到压抑逼仄的船底货舱,从暗流涌动的日常生活到分秒必争的海上救援,影片呈现的每一处影像细节都体现了主创人员对这一电影题材的深入剖析和精准把控。值得一提的是,内容占比高达四成的水下戏份全部采用实景拍摄,其中,不乏复杂多变的场面调度和难度极高的一镜到底,如此引人入胜的视听奇观标志着国产商业制作已经达到了新高度。
光影落幕,片尾出现一行大字——“献给血性的中国人”。电影《东极岛》为观众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独特视角,出色地完成了一次中国故事的国际书写,它让世人有理由去相信,无论历史几经沧桑,人性之光永不磨灭。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
崇高精神的诗化表达
文|徐婧格
与2024年上映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一样,电影《东极岛》取材于中国渔民救援英国战俘的真实历史事件。电影虽与历史原型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但恰是这些距离为具有崇高精神的影像转译提供了诗化的可能。
影片采用了倒计时接力与多视点叙事的手法,完成了动、静、聚、散等叙事形态的动态反复,使影片的叙事节奏与叙事密度错落有致,亦使崇高精神的抒发表现得慷慨激昂而又怆然悲壮。“距离里斯本丸沉没”的倒计时,召唤观众进入历史的平行时空一探究竟,从阿荡救托马斯·纽曼,到阿赑救阿荡和被困的英国战俘,再到阿花率岛民出海大救援,叙事视点的转移与接力一气呵成。影片中杀敌的残酷武戏与悲情的文戏构成了动静形态,阿赑等人的集中救援与吴老大、陈先生、李保长等角色的牺牲,则构成了聚散形态。
在人物塑造层面,创作者在塑造群像的基础上有意凸显了个人英雄主义,以群像建构真实性,以个体建构神圣性。从个体身份来看,创作者虚构了主要人物的身份,无论是阿赑、阿荡、阿花,还是陈先生、李保长等人,皆以外来者的身份进行抗争并完成精神的觉醒,这是一种超越血缘和地缘的身份认同。
令人欣喜的是,《东极岛》以技术赋能电影的文化想象与诗意表达,为观众呈现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一方面,创作团队1:1还原里斯本丸号及岛上的渔船,使用IMAX摄影机进行深海实拍,譬如东极岛海域的水下拍摄、舱内英国战俘的群像拍摄,以及最终沉没和虹吸的场景拍摄,激发了观众的感觉联想,促使“通感”心理活动的生成。另一方面,镜头美学亦时时牵动观众的情绪。随着日本入侵者对东极岛这一“世外桃源”的破坏,影像风格亦从恬淡美好转变为支离破碎,譬如夜葬时的深沉天幕及结尾处阿花的孤舟远影,创构了“孤帆远影碧空尽”的离别之殇。
《东极岛》的故事内核是历史悲剧,精神内核是崇高人格,总体上实现了文以载道的影像功能。这种历经狂风巨浪后回归风平浪静的表达,内含慷慨悲歌之气概,更好地书写了抗战题材电影的价值向度。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
发布于:山东省纯旭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